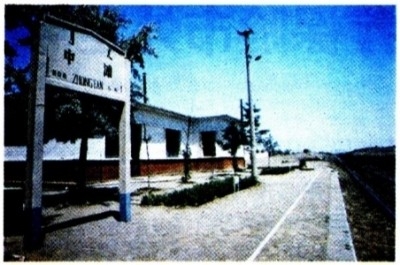
照片中的中滩站是乌达至海勃湾间几个小站之一,于2000年左右撤站,完成历史使命。
斑驳的站牌、空旷的站台、一两排砖瓦房和三两个铁路人,是人们对铁路沿线小站仅有的一点印象。火车在小站的停靠总是急急忙忙,车轮似乎还未停稳,不等旅客看清窗外小站的风景,便又铿锵着驶向远方。
从两代铁路人的讲述中,记者了解了上世纪80年代包兰铁路乌海车务段沿线小站,重温了当年小站铁路职工的工作和生活。
乌海车务段小站知多少
一次到乌海车务段采访的机会,记者偶然看到了包兰铁路沿线许多小站的老照片。车务段工会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1958年包兰铁路建成通车时,包兰铁路沿线仅有桃司兔站、那林桃亥站、碱柜站和乌海北站(原新地站)4个小站。后来,随着铁路运量的增加,为了提高火车的运输能力,陆陆续续建起许多小站,一般在10公里左右就设置一个车站,便于列车的会让。
1982年乌海车务段正式成立时,共管辖着24个站点,小站多为承担会让任务的四、五等小站。从杭锦旗站(原三盛公站)到乌海西站(原三道坎站)的12个小站被铁路人称作“三三段”,这一段铁路紧挨沙漠、风沙大、地形复杂,是包兰铁路线上工作环境最艰苦的一段。乌海北站(原新地站)、源地站、中滩站、黄白茨站、梅勒站、落石滩站和包兰线内蒙古境内最后一站正义关站是乌海境内的小站。
1997年,蒸汽机被淘汰,内燃机登上历史舞台,火车线路由单线改为双线,小站失去了作用,被大面积弃用。从此,小站卸下了历史使命,在铁道线上隐去坐标点。
扳道岔和挂煤油信号灯
1980年,18岁的郭强(现为海老线老石旦站车站值班员)一上班便被派往那林桃亥站工作,成为了一名年轻的扳道员。郭强说:“小站一个班组共5人,一位运转值班员,一位助理值班员,2位扳道员,加上负责小站的工作和职工生活的站长。小站以车站值班员为核心,负责接发、指挥列车的运行。虽然列车有图定到站时间,但有时到站的时间并不固定,所以运转室必须24小时有人。在没车的情况下,车站值班员才能抽空上趟厕所,这时需助理值班员盯住铁轨观察情况。”
据郭强回忆,扳道员的工作也不轻松。扳道员的首要任务就是根据值班员的指令人工扳道岔。“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年龄小,臂力不够,握住柄叉根本扳不动,道岔落不了槽,实在没办法就跳起来用肚子摁柄叉。1987年小站有了女扳道员,搬不动急得女扳道员哇哇哭是常事儿。”
扳道员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挂煤油信号灯。那时候小站没有通电,夜间列车进、出站全凭煤油信号灯指示。扳道员每天在天黑前将煤油灌足,用剪刀将捻子(煤油灯芯)剪好,灯罩擦亮,天一黑就要顺着铁梯子爬到信号机柱上挂煤油灯。进站信号机和出发信号机的灯加起来,扳道员一共要挂11盏煤油灯。六七平方米的扳道房里,地上摆满了煤油灯。灯挂好后,扳道员的任务就是坐在扳道房里瞭望这11盏灯,保证灯不熄灭。这是一项极为枯燥却责任重大的工作,如果火车进站时煤油灯熄灭了,火车司机将无法判断轨道情况,就不能顺利进站,属于小站工作事故。一张桌子,一把没有靠背的板凳,扳道员就直挺挺地坐在那里,左右瞭望信号灯。遇上风大的日子,煤油灯常常被吹灭,站在信号柱上火柴根本点不着,扳道员必须把煤油灯取下来回屋内点好再挂上去,一晚上折腾下来人已筋疲力尽。为了方便瞭望信号灯,扳道室三面都是玻璃墙。冬天扳道室内三面漏风,扳道员冻得待不住,实在坐不住的时候,扳道员就把凳子挪到室内唯一的一面墙下坐着靠会儿墙。日子久了,墙上便被靠出一个槽来。
1987年开始,那林桃亥站上有了硫酸蓄电池,用灯泡点亮信号灯,但小站职工日常生活仍旧使用煤油灯。由于小站没有通电,所有的蓄电池都从巴彦高勒站由充电工统一充电后,放在507客车的行李车上向各个小站发送。小站站长每天将没电的蓄电池递到507客车上,再将充好电的接下来。从此,扳道员的任务由盯煤油灯变成了盯灯泡,灯泡一旦烧了,就要赶紧换上新的。
喝黄河水 风沙为伍的日子
“挎着一个菜篮子,背着面袋子,手里提着军用饭盒子”是铁路小站职工给人的第一印象。小站都设在荒郊野外,附近好几里地荒无人烟,小站人的吃喝都得从家里带。小站人与家人短暂团聚后,土豆、白菜装一篮,米、面准备半袋子,就又匆匆赶往小站工作了。小站实行轮班制,每个小站职工的休班时间不足一天,因当时的通勤车很少,回趟家很不容易。有时小站职工搭乘顺路的货车回乌海,遇上不经停乌海车站的货车,人就被拉到石嘴山去了,在石嘴山车站再等个大半天,换乘途径乌海的客车坐回来。这一来一去,把时间都花在了路上,回到家不等屁股坐热,就该抬脚走了。所以如果不是非回家不可,小站职工大部分时间都在小站度过。
说起小站吃水用水,扳道员郝海林回忆说:“1986年我刚满18周岁,便接了父亲的班,到大羊场站(五等小站)工作。虽然父亲是老铁路人,我多少了解些车站的工作,但被派到大羊场站我便傻了眼,除了几间砖房和毛坯房外,放眼望去就是苍凉,只有呼呼的大风在耳边肆无忌惮地刮着。”站上点的是煤油灯,吃的是黄河水。车务段从离小站最近的村子里雇了一个老乡给小站送水。牵头毛驴套上个板车,车上安个空油桶,就是个运水车了。黄澄澄的黄河水拉来后倒进一米多高的水缸里,等泥沙全部沉了底儿,小站人就用上层的清水洗衣做饭。因为是从农田灌溉渠里运来的“纯天然”的黄河水,小红虫子、飞蛾、几公分的小鱼常常成为水缸里的“不速之客”,时间长了,小站人也就见怪不怪了。做饭的大师傅也是从附近村子里雇来的老乡,只会做简单的饭菜。那时候吃饭也不讲究,没有早点,一天只有两顿饭。军用饭盒是铝制的,不保温。冬天的时候,等大师傅把饭送到值班室和扳道房,饭就凉了,这也是铁路职工普遍肠胃不好的原因。
据郝海林回忆,戈壁滩上风沙大,屋外刮大风,屋内就刮小风。如果大风刮一晚上,第二天一睁眼,满头满脸一层细沙,嘴里的沙粒咬着“咯嘣嘣”响。由于门缝宽,一场风刮过,门内堆着小沙丘,门外堆着大沙丘,顶住门根本打不开。铁道尖轨经常被沙子埋住,清护轨道成了小站职工的日常工作。
考生僻字 看客车打发时间
因为没有电,小站的生活简单枯燥。拉家常、讲故事占去了小站职工大部分的业余生活。郝海林所在的班组里有几个中专生,有人从家里带来一本新华字典,工作之余几个人就翻字典,专找生僻字互相考,逗着玩儿。没过多久,一本字典就被翻得破烂不堪,几个人的汉语词汇量却得到了扩充。
全站人最自觉、最准时做的事儿,就是迎接一天两列客车进站。不等客车靠站,小站上的所有人都会自觉到站台集合,立岗迎接客车。与其说是迎车,不如说是为了看人。蒸汽火车车窗可以打开,到站时旅客纷纷将车窗打开,探出头来看窗外的风景,这也为小站人提供了看过往旅客的机会。“小站的男同志专挑年轻的女乘客看,”郝海林笑着回忆说,“小站职工常年在站上工作,和家人聚少离多,更没有和姑娘相处的机会,找对象成了大难题。‘好女不嫁行车郎’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一句话。”看列车上形形色色的旅客,偶尔和哪个旅客搭个讪,客车短暂的一分钟停靠时间,成了小站最具人气的时刻。当客车拉着长笛轰隆隆驶离车站,郝海林孤身一人回到扳道房,坐在板凳上,失落感顿时涌上心头,“车走之后,小站又恢复了宁静,心里面空落落的,羡慕极了车上的乘客,能潇洒走四方。”郝海林说。
与牧民老乡的深情厚谊
乌海车务段铁路沿线很多小站都与牧区距离不远。平日里蒙古族牧民外出办事会到小站上等车,找车站职工办理乘车补票手续,一来二往的就都熟络起来。热情好客的牧民操着生硬的汉语邀请郭强他们到蒙古包去喝自家酿的酸奶。拗不过牧民老乡的再三邀请,遇上天气好,休班的时候,郭强和同事们便步行两三个小时到草原蒙古包里串门子。牧民老乡给每人倒上一大碗自酿的酸奶,还不忘加上一勺白糖,那酸甜纯正的酸奶味道至今让人一想起来就流口水。虽然在语言上不能畅快交流,但牧民老乡能歌善舞,喝酒更是豪爽。遇上牧民老乡家里有喜事,牧民老乡会杀羊款待铁路小站的客人,酒一满上,歌声也随之响起。蒙古人不论男女老少,都是唱歌的能手。老额吉要是来了兴致,也会一展歌喉,盘腿坐在炕上唱得如痴如醉。郭强虽然听不懂蒙语歌词,但从悠扬婉转的曲调中也能感受到牧民老乡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满草场找鸡蛋是郭强到牧民家做客的活动之一。牧民老乡养鸡不用鸡笼,任鸡在草原上野生野长。草原上的鸡飞行能力相当了得,飞起来人徒手根本逮不住,母鸡专拣隐蔽的草科子下蛋。“草原鸡蛋个头非常大,是地地道道的‘上鸡蛋’,炒一盘炒鸡蛋,金灿灿、香喷喷的,好吃极了。牧民老乡实在,那么大、那么好吃的鸡蛋才一毛钱一颗,而且这价格保持了好多年,5块钱能买满满一篮子草原鸡蛋,是小站职工改善伙食的重要滋补品。”郭强回忆说。郭强心细,知道牧民老乡去趟市区不容易,蒙古包里缺生活用品。他每回去蒙古包做客时,都会带上买好的酱油、醋或者日常生活用品,有时还能带些应季的新鲜蔬菜。牧民老乡很感激,每次要付钱时,郭强都会笑着摆手拒绝。
“那时候小站上连辆自行车都没有,去牧民老乡家来回要走六七个小时,虽然去一趟很费时间,但时间长了就想得不行,馋老乡自制的蒙古酸奶和听不够的老蒙古调调。那歌声好听得直往人的心坎儿里钻,听着会上瘾。”回忆起和牧民老乡相处的日子,郭强发出无限感慨。
“1997年冬天,撤站工作开始进行。许多人坚守在撤站一线,在小站上站好最后一班岗,不知是因为天气太冷还是对小站那份不舍的心情,撤站期间好几位小站站长病倒了。撤站工作进行了一年多,大部分小站被撤,仅保留了杭锦旗站、碱柜站、乌海北站(原新地站)3个站。撤站结束后,驻站的铁路工人被分流到各个车站,继续工作。”郝海林回忆说。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