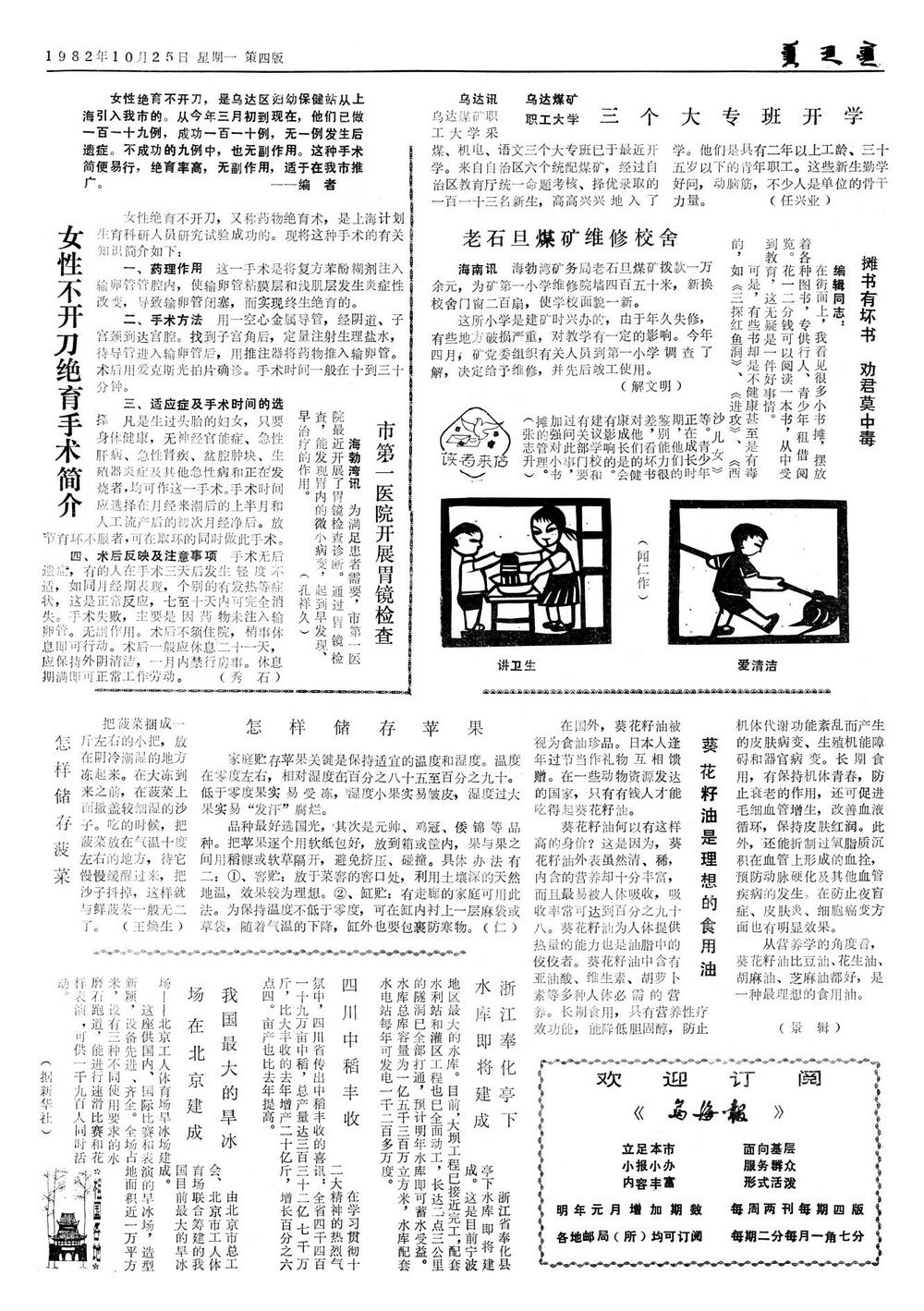
1982年《乌海报》读者来访栏目与读者建立信息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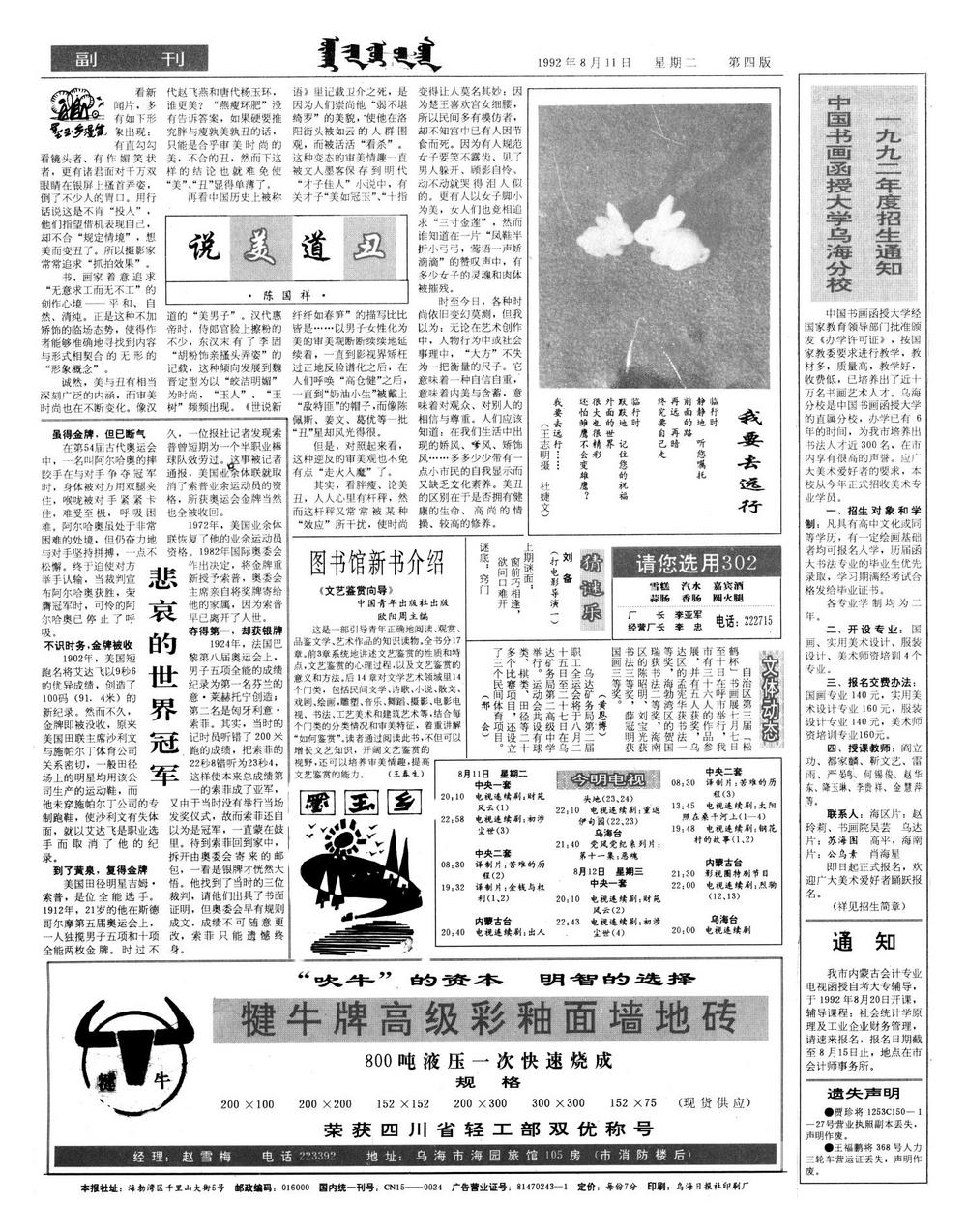
1992年《乌海日报》副刊版栏目——墨玉乡介绍新书。

2004年《乌海日报·双休周刊》版面——阅读。

2014年《乌海日报·晚报》版面——阅读·连载。

作为历史最悠久、普及程度最高的大众传媒之一,报纸,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承担着引导大众阅读的重要作用。
相较于书籍来说,报纸的大众传播效果更加明显,它阅读门槛低、所涉信息广、易携带的同时决定了它易传播,对于很多读者来说,报纸就是他们阅读过的,成本最低但价值却最高的优质文本。
乌海人对《乌海日报》应当有非常深厚的感情。除了因为《乌海日报》在过去四十多年春秋中始终陪伴在乌海读者身边外,还因为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承担着大众阅读的风向标。
曾几何时,我们用“豆腐块”向读者传递外界信息,用铅印字充实读者的精神世界。散发着油墨香的报纸,就如一泓清泉,滋润着无数读者的心灵家园。
“豆腐块”里的大世界
1977年7月31日,在乌海的传媒事业史上,应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这一天,一份飘溢着油墨清香,满载着全市各族儿女重托的《乌海通讯》,在党和人民的期盼中诞生,顺利开启了乌海新闻传媒事业的历史篇章。
但这份四开四版的《乌海通讯》并不是乌海地区的第一份报纸。虽然此前的1958年,《乌达矿工报》已然吹响了宣传事业的号角,但由于其为企业所办,且有地域局限,并不能完全承担起1976年后才成立的乌海市的时代记录者和人民发言人。
因此,当《乌海通讯》正式面世后,立刻就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须知,在20世纪70年代末,大众可以低成本阅读的刊物还非常有限,除了企事业单位自办的职工阅览室外,街面上书店和报刊亭都极少,“读书看报”还是一件很有“门槛儿”的事情。
当时,受条件所限,《乌海通讯》还是不定期出版刊物,每期印刷量不足5000份,想要大面积传阅存在很大的困难。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1981年。伴随着乌海经济社会文化事业的飞速发展,报业也迎来了春天,1981年7月1日,《乌海通讯》的升级版《乌海报》正式创刊,期号沿用了《乌海通讯》的出版序号,即从164期开始。
这是乌海这座新兴的工业城市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份属于自己的报纸。伴随着中国共产党60华诞的隆隆礼炮声,印刷量大增的《乌海报》迅速走进了严肃安静的机关,走进了书声琅琅的校园,走进了机器轰鸣的厂矿,走进了生机勃发的田野,走进了威武庄严的警营,走进了普通百姓的家中。
尽管只是小小一份报纸,但其内容之丰富,却给当时缺乏文本阅读的人们带来了极大的惊喜。《乌海报》创刊初期仍为四开四版,且还是周一刊(即每周出版1期),但当时的编辑记者仍然绞尽脑汁丰富版面信息,画出了“豆腐块”大小的位置来进行“编读往来”,努力与读者建立信息交流。
于是,这最多承载不足百字的小小天地,就成了报纸传递书香最早的窗口,编辑们从雪片般飞向报社的读者来信中选取有价值的内容进行刊登或者回复,“磕磕绊绊”地为读者提供“建议”或者“书讯”。
1982年10月25日,有一位名叫张志升的读者给报社寄了一封信。信的名字叫《摊书有坏书 劝君莫中毒》。他在信中说:“编辑同志,在街面上,我看见很多小书摊,摆放着各种图书,专供行人、青少年租借阅览。花一二分钱可以阅读一本书,从中受到教育,这无疑是一件好事情。可是,有些书却是不健康甚至是有毒的。青少年正在成长时期,他们的鉴别能力很差,看坏书对他们的健康成长是会有影响的。建议学校和有关部门要过问此事,加强对小书摊的管理。”
这封来信就被当日的值班编辑摘取到了报纸上。熟悉这段往事的报社前辈说,那时候读者与编辑们的互动非常频繁,许多年轻人都曾热情洋溢地对“阅读”这件事提出自己的看法,编辑们也热情回应,除了将他们关心的问题一一解答之外,遇到这样“规劝”读者莫为不良读物买单的信件也被归入“有价值”范畴,被见报就显得理所当然。
到了1983年,报纸上的豆腐块已经新增了“读者之友”,这便是今日报纸荐书栏目的“前身”。
在当年5月份的一期“读者之友”中,编辑推荐读者去阅读《现代散文百篇赏析》。这位编辑在文中语重心长地说:“这些作品大多思想内容健康而又有独特的艺术风格,是议论、抒情、叙事、写景等类型散文的优秀代表。《赏析》做到了雅俗共赏,文化水平高的读者可以侧重于阅读原作,文化水平低的读者在读了原作以后还可以看看评析,检查一下自己对作品的领会是否准确,作品的主要特点抓住了没有,自己在练习写作时应该从中吸取哪些有益的东西。前一段各种版本的作文选流传得相当广泛,中小学生自己的范文固然可以看,但是多阅读一些名家的名篇,会有更大的收益。”
这可能是最朴实无华的新书推介了吧。在大众阅读尚未形成气候的当时,一篇新书推介的意义不言而喻。
许多老读者,都曾记得《乌海报》上的“豆腐块”文章。今年79岁的孙长晋老人就曾掰着手指给记者数:“读者之友、编读往来、阅读常规、背书十法、求真之路、开卷有益,这些小栏目都是引导和推荐大众读书的,我年轻的时候每遇此内容,必定要用小刀片裁下来,贴在笔记本上,慢慢读,反复看。”
在20世纪80年代,报纸版面寸土寸金的时候,《乌海报》的报人们就是凭借这种方式,潜移默化地播撒读书的种子,提升读者的阅读兴趣。
被报纸陪伴的阅读时光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乌海报》上的“豆腐块”都没有中断过。即使版面再紧张、内容再多,百字小书评都会隔三差五与读者见面。
那时候的书评也很简单明了,编者往往并不会浓墨重彩去讲书中写了什么,而是简明扼要讲读者应该读到什么。在一篇对《人生哲学ABC》这本书进行点评的文章中,作者就简单写了不足百字。他说:“中国青年出版社即将出版的《人生哲学ABC》针对青年思想实际,运用马列主义基本观点,阐述了怎样正确理解人、人生和人生目的,阐述了怎样正确看待人生历程中的善与恶、荣与辱、顺与逆、生与死等课题,阐述了社会主义的青年应该具有怎样的人生观和人生态度。运用古今中外名言、故事,析理清晰,娓娓动听,是广大青年、团干部、班主任的良师益友。”
受访者李学斌当时恰好就是一位班主任。当时,因为看了报纸上的这篇文章,他也去新华书店买了这本书,定价是0.27元。李学斌记得,这本书他曾反反复复读了很多遍,又将其当作成年礼物送给了女儿,至今还留在女儿的书房里。
“那是我第一次系统地去读哲学。”李学斌说,“这些往事,你们年轻人可能无法理解,我们这代人,对知识的渴求是无限的,但对如何获取知识却是迷茫的。一则真情实感的书评,有时候就是一盏照亮前路的明灯。”
承担着“明灯”功能的,又何止一篇书评。当时,报纸副刊已经办得非常成熟,“墨玉乡”“朔风”“沙枣花”等陆续与读者见面。最初的副刊,并不仅仅是文学爱好者们练笔和发表作品的园地,它还是一片大花园,种植着种种“新鲜”事物。小块头的文摘、新书书讯、书评、读书观等一期又一期地与读者“畅谈”,无数人曾因此受益。
受访者曹伟明也记得自己年轻时最喜欢从报上摘的内容,那是一条窄窄的“中缝”。是的,从1987年开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般被用来塞广告、遗失声明等小信息的报纸的中缝还承担起了“劝读”的功能,编辑们会同时塞进去很多劝导人们多阅读多学习的内容。曹伟明就摘抄过其中的一段,名为《知识重在积累》,内容似乎只有二百多字。“我记得滚瓜烂熟,无数次引用在了自己的文章里、讲课用的讲义里,给学生们的留言册上。”他说。
记者从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源库里找到了曹伟明说的这篇文章。果然很短,只有四句话——
姚雪垠为了写长篇小说《李自成》,用蝇头小字抄录的资料卡片竟达15箱,共2万余张。
明朝顾炎武,每天将自己得到的新知识记下来,日积月累,后来成为名著《日知录》。
司马迁20多岁开始漫游全国,足迹遍黄河、长江流域,汇集大量的历史和社会的素材。他做太史令时,阅读大量的国家藏书,从中整理出许多有用的历史资料,埋头工作了五年,才动手编写《史记》。
达尔文随“贝格尔”号考察船环球考察,记录了50万字的珍贵资料,最后写成了《物种起源》一书,创立了进化论。
寥寥百余字,“劝读”之心昭然。
受访者郭爱霞也记得自己年轻时从报上读过的一篇文章。作者是谁她已经记不清楚了,但她记得,那篇文章写的是关于北京图书馆的见闻。作者去了一趟北京图书馆,亲身体验了馆内的设施、读书环境和借阅流程,这让当时20多岁,刚刚高中毕业的郭爱霞心动不已。
郭爱霞也曾经是爱读书的女孩,但读书这件事,却总被身边人觉得“没用”。她在矿上当选矸工人,下了班在家读已经被翻得异常陈旧的《艳阳天》,母亲嫌弃她“懒”,埋怨她为啥不和嫂子一起去批发冰棍走街串巷赚点零花钱,她没有吭声,内心想的是那篇文章里描述的句子。她对母亲说:“我要继续念书,我要去北京图书馆。”
1992年,已经更名为《乌海日报》的《乌海报》有了全新的阵地来进行阅读引导。它一度也挤在中缝里,名为“锦言录”。虽然当时报纸承载的功能已经非常多,信息量巨大,且版面更为紧张,但“锦言录”却长期存在。名人名言、寓言警句,名家论述,简短的文字朴实自然地为读者提供着养分和写作素材。
副刊中甚至还辟出了专门的阵地,刊登图书馆新书介绍,第一期推荐的便是市图书馆新进的一本书《文艺鉴赏向导》,编辑在推荐词中说:“读者通过阅读此书,不但可以增长文艺知识,开阔文艺鉴赏的视野,还可以培养审美情趣,提高文艺鉴赏的能力。”
除此之外,报上刊登的其他信息也在为引导阅读贡献力量。比如在1994年的一期报纸上,就有一则消息很显眼,题目名为《怎样给孩子买图书》。
几番改版,阅读终成“悦读”
2024年4月,第三届全民阅读大会在云南昆明召开,在本次活动中,有一个子项目叫做“报业媒体助力全民阅读优秀案例征集”活动,《乌海日报·悦读》被自治区报业协会推荐参与此项目。在活动举办的20多天里,在一名注册用户只能点赞1次的情况下,《乌海日报·悦读》收获了全网5.5万的观看量和6275个点赞。
这是对报业引领全民阅读事业的莫大肯定。
从20世纪80年代“有报”开始,几番改版,几番演进,《乌海日报·悦读》终于形成固定形式,以专题版面的形式呈现。
这期间,也走过了若干年的探索之路。20世纪90年代中期,《乌海日报·双休周刊》《乌海日报·科教周刊》都曾先后推出阅读栏目,这些栏目均以引导全民阅读为目标,记者编辑们通过采写乌海人的读书观、分享好书书评、文艺评论、新书推介等方式将其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密切结合起来,其内容涉及方方面面。
2005年1月5日,《乌海日报·晚报版》正式创刊后,更是以“阅读·生活”“阅读·社会”等形式将阅读栏目扩充为专题版面形式。彼时,版面推荐好书如云,长篇、短篇新书连载读者众多,很多读者都记忆深刻。
2018年,伴随着报纸事业改革,对开四版的《乌海日报·周末》以“书香”的形式继续引领阅读思潮。在若干块“书香”版中,编辑和记者们始终在倡导大众阅读、亲子阅读上下功夫,每期的“好书推荐”“乌海人的读书观”等栏目备受好评。
2021年,“书香”栏目再次改版,按照每周一期的频率在《乌海日报》7版呈现。版名为“悦读”。改版后版面内容更加丰富,立足读书、藏书、评书等多个角度,讲述书里书外的事。
每期的头条稿件,致力于营造全民阅读氛围,通过呈现不同读者的阅读态度,阅读方式、阅读方向以及推荐阅读书单等方式吸引和鼓励全民阅读;“书评”栏目及“好书推荐”栏目则结合当下的文化热点以及读者自身的阅读关注,给读者提供最新最重要的读书信息和相关线索,内容包含文化、文学、时政、历史、财经、学术、养生等图书的最新信息以及内容介绍,注重新闻性、可读性和服务性。
借助融媒时代与读者互动的便捷性,版面设置可以随时关注读者兴趣的变化。无论是头条内容采写还是书摘、书评、荐书选择都能更为注重读者的需求,“悦读”栏目,也成为了主流媒体引导全民阅读的优秀示范。
倘若您要问,在这个数字阅读占主流的读屏时代,报纸阅读是否还有吸引力?
我想,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
无论何时,报刊引领阅读的导向性和权威性都值得一代又一代报人的全力付出。在这个多载体、多元化的融媒时代,报纸更能发挥栏目、活动、新媒体、组织机构建设等整体优势推动全民阅读,通过开辟阅读专栏专版、举办阅读推广活动、创办数字化阅读新媒体等方式,起到对全民阅读事业的组织传播和宣传推广的功能。
我们相信,在流淌的时光深处,报纸仍然有温度,铅字依然有力量,那些白纸黑字留下的记忆,会帮我们记录历史——
山河不改,岁月绵长。
评论